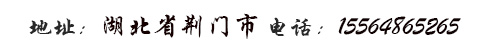散文诗非处方用药之第六疗程
|
作者简介:爱斐儿,本名王慧琴。医生,诗人。年出版诗集《燃烧的冰》,出版散文诗集《非处方用药》《废墟上的抒情》《倒影》。曾获“第四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”、“首届河南诗人年度奖”、散文诗集《非处方用药》获“中国首届屈原诗歌奖银奖”。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多种报刊、杂志,入选多种诗歌年选。先后主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现代青年》、《诗歌月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杂志的散文诗栏目,特邀兼任《大河诗刊》副主编、《诗歌风赏》编辑、《诗选刊》责任编辑、《大诗歌》编委。“我们”散文诗群核心成员。 ▼ 爱斐儿 海棠她在冬天的飞雪中埋下一颗孤胆,推开典籍,温暖每升高一寸,寒冷就降低半分,她站在冷暖之间。 一条路开始启动春天,一双如花的眼,先要看破红尘,再看穿天涯之中咫尺之短,不留给空虚哀叹光阴逝水。 一直都在后退中前进,终于听到一阵风声,把一树花开推进早春的门槛。 路遇雷声两点,细雨三钱,风和日丽的日子数串。只听钟声滴答,想起了时间,她已走过祈祷的侧面。 再唤一声春风,云海开始漫卷。她不预言,短和美。 她只把积攒的花香洒向三月的人间。 芍药解开一枚胭脂扣,半支梅花香隔开岁寒。 一阵雷声,除净风沙的角质层,早春的容颜现出水波的光感。 她在别处。面对一面镜子独自苏醒。 干净的衣裙不沾凡尘,面对一个季节的敏感与嬗变,清理云翳,素面朝天,不用春光的明艳拒绝夜的黑。 ——如果长夜需要黑暗的陪衬,如果梦境能延长一段绝世的爱情,她愿彻夜梦游。用一场大梦找到渡口那只系船的缆绳,解开那颗水手结,找到一把浆声。只轻摇,不弄出水花四溅的波澜,亦不看两岸的长亭和短亭。 听到你的轻唤:“媚娘”!她笑意盈盈,弃舟上岸。 哦,此处离贞观不远。 紫花地丁她保存每一粒种子生存的方式与气节,只把秘密封存于沉默,她深知招展的部分,大多与昙花一现有关。 她把词语深埋泥土。埋下生与死、明与暗、恒与短。并收藏根须、腐烂与重生,只等春天来扣门环。 “你好,春天”。 很轻的语言,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她对人间的热爱,一颗心从此高过了春风化雨。 ——虽然她紫色的花朵,微露风寒,依然高贵地越过了冰封的羁绊。 大地之上,季节的秘密若隐若现,比如附地、泥胡、车前草……已经纷纷跑出地面,这些卑微的草芥,顺便搬来了碎语与闲言。 当然,地丁百毒不染。 她只静静擦拭春风,让天空蓝得蔚然,让大地紫得烂漫。 二月兰时间另有故事留给空间布局谋篇。 就像二月兰、委陵菜和紫花地丁,赠二月以最自然的色彩,白天念着,夜晚梦着。 你看,一路盛开的迎春与连翘,如果你忽略了细节,就会陷入金黄的误区。 谁能拒绝世间的美好,被冠以春天的名义?允许一夜春风以轻盈的名义携带花粉,允许一座花房以缤纷的名义赠你一世的烂漫? 当然,暂且按下露浓霜重中的秋天。 你必须趁天色尚早,备下丰盈的体态与曼妙的舞姿。并在来日方长之间,筑就琴台。 等空间安排时间就绪,等涛声回归波澜不惊,打开琴囊与诗卷,你让琴弦流水,我让月色飘香。 我们不管夕阳西下。 槐花风声一直很软,这个春天。一个深陷美景的人,被很软的春风偷走了心肝。站在长路与短路之间,恍惚的神色,被一棵水荀子和一棵金银木看穿。 她放飞漫天玉蝴蝶,给你看一场亦真亦幻的爱情,如那漫卷的诗书,飘着线装的清香。 她自酿深情,凫渡于似海之念。日日惦记着大醉而归的人,心疼得比花香更深。 很像一段好年景,站在时间的起点,只谈花开不谈花谢,只谈风调雨顺,不谈命运布下的灾难与荒旱。 起因无非两点:更深的美约等于梦幻,更恍惚的神色约等于自然。 就去爱你。。等不来被爱我等在文字那端爱斐儿:名家评论精神王国的建构 ——论爱斐儿散文诗的精神架构 罗小凤 [按:或许是距离太近了便不敢轻易言说的缘故吧,我和爱斐儿的关系情同姐妹,关系笃深,却在她的两本诗集出版后都未曾留下片言只语,不是不想说,而是无法说,不敢说!太熟悉了,反而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至今依然记得我和她在鲁迅文学院初次遇见的情形,那次是阿毛和我约娜仁琪琪格去鲁迅文学院看夏雨等朋友,而娜仁说她和哈森约了去爱斐儿的小月河看看,我和阿毛说我们先去鲁院,改天再一起去小月河吧,她们答应了,于是有了第一次的见面。一见如故。之后便是难舍难分。离开北京时有多么不舍,每次去北京时都是她们接待我,陪伴我,而在我遭受人生最惨痛的日子里,我首先投靠的就是她们,我在她们那里疗伤,逃避,她们给了我最温暖的疗伤角落。那些友谊!那些亲人!每每在遥远的西南方向回想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,心中便无限慨然。而有些话藏在心里太久了,还是不得不说,不然就如哽在喉,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。] 第一次遇见爱斐儿是在鲁迅文学院,一见面,我便被她雍容典雅、淡定从容、静水流深的气质吸引住,无论是话语、动作,还是神态,都是舒缓有致,轻重有度。这或许跟她既是医生又是诗人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,其养生、养心、养气的生活之道化入诗中,让她在文字中建构起一个独特的精神王国,正如她自己所坦陈的:“爱上诗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!她让我的世界无端多出了一个辽阔无际的空间”[1]。在这个纸上王国里,她是君临天下的“君王”,人间草木都是她的“文武百官与子民”[2],文字是她的刀枪剑与权杖。爱斐儿以这个精神王国对抗如临深渊的孤独感,尽情展开心灵的舞蹈,在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疗伤与救赎,或许正是因此,她与她的诗获得了独特的气质与气场。 孤独感的对抗 写诗,是很多诗人用以对抗孤独的一件有效武器,爱斐儿更是将这件武器运用得物我合一、器神一体。写诗让她“生长出强健的心肌去对抗孤独感的夜袭”,“在一种如临深渊的孤独感中,她帮我平息庸恶世事与高蹈精神间的风暴”[3]。无论是爱斐儿的《非处方用药》还是其《废墟上的抒情》,以及她目前正在进行的其他散文诗创作,都是她用以对抗孤独感的秘密武器,她以诗为兵,以文字为剑,开辟了她自己的江山,建立了自己的王国。 依据存在主义哲学,人本身就是一种孤独的存在,正如海德格尔的“被抛理论”所指出的,人是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在世的,他绝对地孤独无助。[4]孤独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之一,生命就是一种孤独的存在。与生俱来的最本源最重要的生存体验,便是喧嚣尘世里的深切的孤独感。人被莫名地抛入这陌生的世界,孑然一身孤立无援。而在现代,孤独感更成为通病。正如弗洛姆所说:“在现代社会中,个人刚从曾经使生命具有意义和安全的所有束缚下解脱出来,就陷入了孤独、无权力和不安全之中。我们已经看到,人是不能忍受这种孤独的,作为一种孤独的存在物,人是无力与外部世界抗衡的。”[5]现代社会使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越来越疏远和对立,人,成了孤立的个体,失去了安全感。甚至可以说,孤独成为人存在的最本质状态。 面对孤独,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日本著名心理学家箱崎总一把孤独分为两类:消极性孤独和积极性孤独。他把能借助与人交往、共处而解除的孤独称为“消极性孤独”,而把有助于创造、发展的孤独命名为“积极性孤独”;他认为“消极性孤独”者是以强烈的依赖心,希望借着与他人交往来消除孤独的想法为中心所形成的,人只要停留在这种“消极性孤独”的阶段,便难以独立,无法确立自我的自主性;相反地,“积极性孤独”是不打扰他人,自我判断,自己冷静探讨人生前途时的必要状态,能存在于“积极性孤独”中的人,必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[6]。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忍受孤独寂寞,承担起孤独的重力,以孤独为支点,托起人生的生命重量,从而超越孤独,升华孤独。无论集体还是个人,超越孤独都是非常重要的。“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,如果没有忍耐孤独的精神,和缺乏控制孤独的创造力,则无法存在于社会。”[7]确实如此,大凡有所成就者,无一不是能甘于孤独,并能享受孤独,利用孤独,化孤独为力量的孤独者。尤其对于从事创作的人而言,“孤独是创造的原动力。”[8]创作者们在孤独中都以文字为武器来排遣孤独,救赎孤独,超越孤独,在语词里构筑心灵世界凌驾于孤独之上的精神空间。他们将孤独感由我及彼上升为整体性的、有意义的精神情愫,将纯粹个人的孤独升华为对全人类普遍孤独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ihuadidinga.com/zhddpzff/1099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悬壶济世中医妙方汇总十一十二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