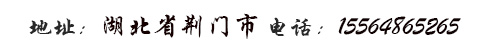沾花惹草
|
一 一九七九年升入家乡小镇高中,为了学好语文,应对高考,又无闲书可读,同学之间兴起了一阵背诵热,重点就是“新华字典”和“现代汉语词典”。 读着背着,汉语词汇量不知不觉就增加了。为了某个字、某个词,有时还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。 “沾花惹草”,“粘花惹草”,还是“拈花惹草”,就惹起了花花草草们的热烈辩驳。语文老师的裁定好像是“拈花惹草”,但并没有定分息讼。 阴冷的冬天终于过去,春风骀荡,花草明媚,何不团香弄玉,沾花惹草?我坚定地站在沾、惹的一方。 那会儿,小镇东部、陇海铁路北边的中学校园垂柳丝丝,高杨鸣蝉,青桐亭亭而立,法桐遮天蔽日。白墙青瓦的一排排教室之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树篱,摘一片圆圆的叶子,揉一揉,一股青苹果的味道。 出了校园,附近是大片大片的农田,春天紫花的地丁,白花的荠菜,金黄金黄的油菜花,还有东边的柔桑紫葚,北边的一泓碧水,西边高墙中的白杨和公社粮站仓库,南边的风荷剑蒲和陇海铁路上呼啸而过的客车货车。 那会儿,上下开始拨乱反正,花花草草正摘去封建主义、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邪恶标签,校园中的花花草草也朦朦胧胧地人性觉醒、情窦初开了。 二 家乡地处黄淮平原,人口密集,村庄星布,农耕发达,每一角土地几乎都被人们过度开发占用了,草木种类当然不如山区丰富多样。不过,堰边水畔,墙头瓦垄,但凡有点土壤,就能顽强生长着一些知名不知名的杂花野草。 杂花野草不只是天地之间的美丽点缀,还可以春夏作家畜的食料,秋冬是烧火的柴草。诸如灰菜、苋菜、马齿苋、蒲公英、猪耳菜、芝麻草、苦菜、苜蓿、抓根草、水浮莲、绿萍、薯秧、棉籽、槐花、榆钱等,都是自小熟悉,时时挖采,常常沾惹的草芥,在三年大饥荒时还救助过亿万百姓的顽强生命。 还以爱花为名,挖来了刺玫、半夏、红蓼、黄菊等野花,种在小院。在我的精心照料下,她们原本山清水秀,勃勃生机,慢慢地面黄肌瘦,残枝败叶,亦如麻雀、野兔等鸟兽,野性的生命实在难以接受人类的驯化和控制。 三 离乡进城,读书工作,或南或北,寸心千里。四壁钢筋水泥,一天乌烟瘴气,到处指标数字,时不时地也就重拾旧爱,莳花弄草,梦想着回不去的昨天和土地。 记得过完大学第一个寒假,曾将家中容易生长的韭菜兰、仙人球等带到学校,栽入小盆,放在窗台。下课后,无梦时,看一看,聊慰乡思。 如今,阳台还摆放着好多个形质各异、大小不一的花盆,凌乱葱茏地生长着绿萝、茉莉、吊兰、仙人掌、虎皮兰、滴水观音等一些老实泼皮、不常开花的南北植物。 养过两盆普普通通的君子兰。一源于亲戚,一赠自同学,小二十年了。偶尔浇浇水,换点土,最初几年一碧如玉,后来岁岁凌寒开放。 不管忙闲忧乐、风狂雨骤,不管飞鹰走狗、天寒地硬,人源自自然,归于自然。每一个理性的个体都应当隐藏着野性和感性,每一种进化的生命都应当趋向光明和勇敢。只要活着,生活中怜香惜玉依旧,沾花惹草永远! -03-08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ihuadidinga.com/zhddpzff/1064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治无黄疸型肝炎疫苗后遗症都可以用的一个
- 下一篇文章: 涿州周边占地亩将建设湿地公园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