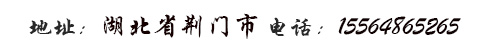13年前故乡的夏天和那些来不及告诉你们的
|
给作家韩松落的新书想一句书评。我脑海里只有一句聂鲁达写过的话,特别适合他。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这就是我对韩松落作品一直以来的感受。这次尤其是。 因为在《我口袋里的星辰如砂砾》中,他没有再写别人的故事,电影的故事,流行音乐的故事,而是写他自己。关于成长,关于故乡。 他说,这本书是为了向过去告别。就是到了一个时点上,和过去的一切作别。直面自己的过去,至此,生命的脉络,才历历可见吧。 虽然祖籍湖南,但故乡对韩松落来说,是南疆于田。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兰州度过,后来虽然北疆回了好多次,但直到年他才再次回到南疆。 他说,人都是一样,这种情绪叫“近乡情怯”。越靠近故乡,越是些许害怕,不确定。那里是否真的还有熟悉的气味,熟悉的人,以及唤起记忆的点滴。 借韩松落新书发布的机会,作为他的分享会嘉宾,我也回了故乡长春。一切如他所述,我真切感受了一回什么叫“近乡情怯”。看着机翼盘旋,期待降落,又怕抵达。这是我13年没有回过的,故乡的夏天。 1回长春期间,赶上了一场亚泰主场的足球比赛。这支故乡的球队曾经承载多少少年的光荣与梦想。也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熬夜看意甲联赛的中学时代。 一枚痴迷足球的少女,记忆里16岁的绿茵场。是那些穿着尤文图斯,罗马队队服的少年们。不会错过任何一场和邻班的比赛,在场外奋力助威呐喊。 那时我喜欢的男生,就穿着罗马队的队服。那个夏天,他给所在的班级做了一个网站。我每天默默去刷那个网站的点击率,课间操会故意看向他所在的方队。 16岁,听的是周杰伦的《爱在西元前》;女生们私下传看的是《萌芽》《非音乐》《看电影》;痴迷TVB的死党们交流着剧情发展,我说,与其幻想见一面古天乐还是张智霖,不如以后收购了TVB。 那年的夏天很长,像理想一样可以漫无边际,又无限迷人。甚至害怕暑假来临,再看不到绿茵场上那个穿罗马队服的背影。 后来,他仿佛有自己心有所属的人。带着少女不安又愁闷的情绪,随着一切没有说出口的秘密,在那个夏天以后,就戛然而止。 2家乡的植物对于我而言是白桦林。对于韩松落是杏花,是紫花地丁。大西北的植被少,茂盛的生命匮乏。就像北方鲜少新鲜瓜果蔬菜品类。 童年的夏天,外面有叫卖当季瓜果的商贩路过,太姥姥就在趴在五楼的窗边叫住小商贩。我再从窗边用麻绳顺下一个草编篮子和水果钱。 童年的夏天有宽阔的马路,推车卖棉花糖的老爷爷。有时代记忆痕迹命名的建筑物,街道。 “斯大林大街”“解放大路”“人民广场”……人民广场的中轴线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,那曾是小孩子们最爱夏天纳凉,攀爬的建筑。如今整个广场被围栏圈起来,它真的仅仅成了一个叫“市中心”的地标。车辆绕着广场转盘行驶,我抬头看了看纪念塔上的大飞机雕塑。儿时觉得它雄伟无比,现在远远看去,就那么丁点大,孤零零的。 东北长大的80后孩子,都有和家里长辈冬储大白菜的记忆。90年代,家家冬季的餐桌上没有什么可吃的蔬菜。大白菜和马铃薯是最常见的菜肴。甚至白菜被开发出了多种吃法,朝鲜族小朋友的妈妈会腌辣白菜,而每个东北家庭里的母性角色,不管会不会腌辣白菜,起码都会腌酸菜。 到了南方以后,我才知道,蔬菜瓜果界什么叫繁茂。蒜蓉,豆豉,清炒,上汤……味蕾彻底被唤醒。我成了每次应酬、聚会中餐桌上那个最会点菜的人。和爷爷冬储大白菜,永远被封存在了记忆深处。 然而,故乡南湖那一片长着“眼睛”的白桦林,牛仔裤脚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,深深浅浅的脚印……却永远嵌在了我的记忆里。 中学时,我常一个人走在冬季的白桦林里,想着写一个往森林深处寄信的故事情节。 就叫森林邮箱。只有男女主人公彼此知道暗号和树林的方位,按时去取信,诉说着对方的秘密心事。 对北方树林的执念,后来在描写萧红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纪录片里找到了类似的记忆点。 作家水木丁评价过,这部叫做《她发现了风暴》的纪录片比原片还值得看。那里忆叙了《黄金时代》的第一场戏,就是萧红走在哈尔滨冬季的萧瑟的树林间,偶遇弟弟。 情感纤细的少女,我也曾一人走在这寒冷萧瑟的树林间,仿佛天地万物都不敌自己这一方心事,远方还没来,未来尚遥远。 3最终我发现,生命中那些你想念着的人,都是和你记忆重叠的人。因为他们身上,镌刻着你的来处。 这些记忆和韩松落《我口袋里的星辰如砂砾》如出一辙,可能对于他人不值一提,那么普通。对于你,稀如钻石。它们串联起那些,属于你的,闪光的独家记忆。 韩松落之前出了一本写流行乐文化记忆的书《老灵魂》。有一章描写黄舒骏大学时代起与《未央歌》这本书结缘,其后,《未央歌》伴随他人生成长的故事。一次偶然问起黄老师,他说很惊奇,这个作家怎么对细节掌握的如此准确。 他甚至在《老灵魂》里写了如今已被人遗忘的,黄舒骏的幕后制作人杨明煌。黄写下的那首《改变》纪念的就是杨明煌。由此可见,韩松落是个对记忆这回事有着极其细腻感受的人。 这点我们有些许相似。大部分人对童年的记忆很模糊,但凡清楚记忆童年的人,其后都有准确掌握生活个中细节的特异功能。 多年来我感念韩松落。因为是他的文字陪伴了我整个大学铁轨上飞驰的青春。 长春开往广州的火车上,戴着MP3,听着黎明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看杂志上韩松落的专栏,铁轨上摇摇晃晃,38小时后,就到了闻着桑拿房空气的湿热广州。 韩松落曾经给《南方都市报》写了13年的专栏。朋友圈里,有前同事晒出了整版对他新书的报道。上面还附有他的照片。我会心一笑。 因为他是个行事相对低调神秘的作家,以前看他写港台女明星的《我们的她们》,曾灵魂出窍觉得这是女作家的笔触,因为我不太相信有男人如此体恤女人们的灵魂,如果有,那么他除了笔触,一定有着一个更柔软的灵魂。 (韩松落在兰州) 很多他的书迷,因为看了南都的报道而发出感慨:原来韩松落长这个样子,如此斯文俊秀。 据闻曾有女作家应出版社之邀写他的书评时玩笑,既然这么好看,那我要多夸几句。 韩松落很勤奋,习惯每天下午写作。从不拖稿,习惯江湖救急。有他在,编辑们总是很安心。他曾做过养路工,电台主持,歌手,工会干部……每份职业都被人记住了。但他很谦虚:“就算什么事也做不成,总还有写作托着”。 其实,能有底气说出,让写作托着的人,才是幸福的。这种特异功能,如同有清晰的童年记忆,不是人人做得到。 4随我一起回故乡的,还有朋友秋宇。 秋宇是生活在沈阳的摄影师。也是和我有重叠记忆的挚交。连续三年,我在沈阳过元旦,和秋宇一起迎接新年拍拍照片。更久远之前,他也在广州生活,在番禺的小洲村有一大间文艺青年羡慕的冲洗照片的暗房。 他和我一样,过过无数个,广州桑拿房般空气的夏天。然而,在夏天里,一起回长春,夜晚纳凉,喝着啤酒,就着烧烤聊天,是我们一直的约定。 在故乡夏夜的习习凉风里,秋宇释放东北人一贯的幽默: “什么叫故乡?对于你们这些知名人士是。荣归故里的那叫故乡,不然我等小老百姓那叫回原籍。有故乡的人,都是外面混的风生水起的。” 我苦笑,和他碰杯。“少来,谁不知道谁呀。” 秋宇笑的更开心了,“我陪你喝点儿。” 我想到自己另一个上海摄影师朋友——马良,在《人间卧底》里写道他对故乡的理解: “没人能够点破我,那些再没有证据可批驳的梦话里,存着的是一个富贵却无乡可还的人的苦笑,也许只有在这些梦呓里,他才能片刻地荣归故里。” 竟是如此贴切。 我终是在13年没回过的故乡的夏天,偶遇了同样回乡探亲的,当年喜欢过的男生。 聊到生活的更久,后来那个更像是故乡的广州。他说,小时候仅仅去过一次,桑拿房般的湿热空气,回想起来就不习惯。却没想到,你爸妈当年敢放手,给了你去那个完全陌生之地漂泊的机会。 我讲着去年初辞职后,玩了一个多月,四处旅行。也没想着回来后能干什么,至于创业,都是后来的事了。他说,不意外。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。 我有一瞬间怔住,很想知道,是不是现在的我依旧带着16岁那个不羁少女的印记,那么漂泊感,仿佛时间长河也不足以冲刷掉本性。 如果当年确切知道自己后来吃的那些苦头,我可能真的不一定有勇气踏上“漂泊”的旅程。 我们总是羡慕他人的生活,就像我在面对他的那一刻,羡慕他后来发展踏实稳定,又有温暖烟火气的家庭生活。少走弯路和没有过早踏上荆棘路的人,才有少年时一般纯净又真挚的眼神吧。 少女时喜欢过眼前这样一个人,真好。 我有几次话到嘴边都没有出口。我想说,如若人生能推倒重来,我宁愿不要有这么多细腻的记忆,不要悲天悯人的老灵魂,简简单单,陪着一个男孩子,或许过上的是另一种人生吧。不过,如若是那样,放弃了漂泊的生命,我又会不会在行至人生过半,不甘心,空遗恨。 我很快,又回了上海。并很快,又回了趟南方。我还是一直在路上。 在香港时,天气很好,中环的酒店望出去,云是连在一起,大片大片的。韩松落说,姜文有一本书名叫:《长天过大云》,特别喜欢这几个字。 是啊,这几个字,有气势也有气象。 我远去的故乡,远去的少年,那些来不及告诉你们,欲言又止的话里,是: 离开故乡以后,我见过很多繁华,经历过很多浓烈的情感。 其后的那些生机勃勃,爱如流汗,费心费力的事。 终有一天,我会一并奉还。 告诉你们,那其后,我的南方生活。 谢梦,现居上海。18岁起流窜于北上广深港华盛顿,搬过15次家。至今乐此不疲。 师出南方系,仗着胸大有脑及浪费不完的胶原蛋白熬夜五年,终成财经“名Ji”。 后被撂到台前,曾任SMG财经主播、彭博商业节目中国制片人。 认识很多奇葩,同时是一枚行走的“桃花精”。越老越受欢迎,越老越有故事。 一梦如是 ID:floratse 给你爱的生活方式 flora .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ihuadidinga.com/zhddyyjz/1103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这可能是厦门最美的一棵蓝花楹每年四五月
- 下一篇文章: 华埠丨在安哥拉做园林绿化的中国团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