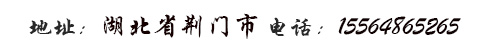寻常里的故乡通元夏家湾夏永军
|
随笔散文 年7月,夏永军《寻常》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—— 夏永军,海盐通元人,从事散文、小说创作二十年余,作品散见于《江南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西部散文选刊(原创版)》《雨花》《烟雨楼》,还多次被人民网、学习强国转载。用文字回望记忆里的乡愁,咀嚼寻常日子里的味道。 人生旅途中,最有价值的遇见,是在某一瞬间,重遇了自己,那一刻才会懂,走遍千山万水,无非是淌一条通往内心的河湾,顺流而下—— 01 我一直想写篇关于家乡“夏家湾”的文章,以纪念少时那段与之朝夕相伴的岁月。我问询过生产队里好多上了年纪的老人,仍无从考证“夏家湾”这个地名的出处,或许海盐秦朝设县建制时,“夏家湾”这个地名就早已存在了吧。海盐地图上觅不到这个地名,有一回,我在谷歌全球眼上却清晰地发现夏家湾狭细如眉弯的河浜形状。《康熙字典》上释义:湾,即水流弯曲的地方,通元武通港流经韩家桥往东时,在此处拐了个弯,向东侧内凹半里,形成了一个河湾,便是“夏家湾”的由来。夏家湾,俗名夏家浜,在文革时又被赋予了另一个名字“红星”,沿用至今。夏家湾以“夏”为主姓,湾北还有何姓,湾南只住沈姓人家。我家世代住在浜北岸,枕河而居。我爷爷和两个小叔住的屋宅坐北朝南。我父母的屋宅坐西朝东,我父亲是做上门女婿的,这里面有个插曲,七十年代初,我爷爷因两个小叔尚年轻,怕我母亲嫁出去,失了劳动力,撑不起一家子,故强留我母亲招上门女婿,托生产队一嫁出去的姑娘做媒,结识了邻村一做裁缝的小伙子,入赘了我家,那便是我父亲。听我母亲说,以前我家祖上也蛮殷实的,太爷爷把家产交到爷爷手里时,队里还有不少房产,谁知我爷爷年轻时迷上了赌博,成天到晚搓麻将,把大半祖屋败光了。父母住的屋宅连年漏雨,一到下雨天,家里锅碗瓢盆全用来接雨水,屋内叮叮咚咚地响成一片,在年幼的我听来,却像是奏乐。可年轻的父母那个愁啊,怕啊,一到台风来时,房顶被吹得咯吱、咯吱响,父亲怕屋子被刮倒,拿几根长树棍,顶在西外墙头。我和姐听着呼啸的风声,半夜还蜷缩在母亲臂弯里,不敢睡去。腊月里,父亲冒着风雪,和小叔去六里堰石矿的河里摸石头(河里的石头不要钱),一大早出门,黄昏时,船还未归来,母亲焦灼地守在浜口张望,天黑透时,迷蒙风雪中,只听见悠远的“欸乃”摇橹声隐隐传来,船终于沉沉地摇回来了。母亲握着父亲浸泡得通红的手,眼泪簌簌流下来了。翌年开春,父亲终于在生产队最北面的空地上,盖起了四间瓦房,结束了我和姐担惊受怕的日子。▲父亲在看书,他不识字在我记事中,却从没见过爷爷搓过麻将,他倒有一绝活,常铭记我心。他擅长用棕麻和竹叶编蓑衣,分棕蓑衣和竹叶蓑衣两种款,前者棕毛缝制,结实耐用,被雨淋后稍重,穷一些的人用不起。竹叶蓑衣轻便,便宜,但不耐用。爷爷还编笠麻,竹篾编成,夹以宽大的箬竹叶,用以遮阳挡雨。清明刚过,爷爷就在煦暖的屋檐下忙碌开了,将上年从棕柳树上割下来的棕麻晒去霉味,然后绞成一股股的细绳,又用一根细长的针,穿上棕线,麻利地缝制起来,一直忙到梅雨季来临前。爷爷家屋后有一片茂盛的箬竹园,茂林修竹间,终日竹影婆娑,箬竹叶宽且厚,也用来裹端午粽子。黄梅时节,雨纷纷,生产队的社民们穿上爷爷缝制的蓑衣,头戴箬笠,细作在田间地头,真是一番“青箬笠、绿蓑衣、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繁忙景致。父母收工回来时,蓑衣湿漉漉一片,被高挂在廊檐下,滴沥着雨水,风吹洇干,而里面却是干燥着。爷爷还会编草鞋,他编的草鞋,经久耐穿,我记得小时候也央求他给我做了一双,方便我下雨天,在泥地上撒欢跑。02 爷爷家西隔壁住着一户何姓人家,何老太有着一双三寸金莲,终日踮着脚尖,撵着碎步细细走路。她有很深的洁癖,屋子里终日闭着门户,阴暗、幽深,却总擦拭得一尘不染。何老先生有一独门绝艺,擅编殡葬纸制品,他编的纸屋、纸车、纸家具,活灵活现,栩栩如生,涂的油彩妙趣横生,因开价公道,我总看见丧客大老远地慕名而来,络绎不绝。有一年他谢绝了丧客,独为自己和老伴做起纸殡品来,直至堆满了一屋子方休,令社民们疑惑不已。他先于何伴过世了。出殡前,何家孝子贤孙浑身缟素,披麻戴孝,高声恸哭,在泥场上将大半屋子的纸殡品焚烧了许久、许久。何老先生的第四个儿子参军退伍后,转业在上海闵行。记得我小时候,叔从沪上回来时,总会带来好多上海高级奶糖,微笑着向社民们分发,这个时候,何老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,鬓角集结了深纹。母亲说知青上山下乡那回,曾有一年轻女知青插队在爷爷家,她叫白梅,长得清秀、端庄,而且会唱昆曲,每天清早,白梅都要到河边,对着幽静的湖面,甩着轻盈的水袖,翘着秀逸的兰花指,吟唱开了: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!朝飞暮倦,云霞翠轩;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。白梅清丽、婉转的唱吟,在清晨的浜面上,被清风吹得细细曳漾开了,在河埠头浣洗的勤劳农妇们,停止讪聊,听得入神,忘却了洗衣、淘米。我母亲那时才十五六岁,和几个队里的女孩子,早晚央求着白梅教昆曲。打猪草时,女孩们放下镰刀,在田埂上将昆曲唱开了,唱错了互相纠正,唱偏了相互指点,还比谁的兰花指翘得地道,谁的水袖甩得有味。傍晚,她们一放下碗筷,便簇拥进了白梅的房间,白梅将昆曲的历史和《牡丹亭》里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凄美爱情故事娓娓到来,姑娘们听得脸颊绯红。不久,隔壁生产队一个叫菊生的小伙子喜欢上了白梅,紧追她,但白梅早心有所属,菊生吃了闭门羹,心郁不快。菊生向县里偷偷举报了白梅在队里唱昆曲的事,上面定性白梅行为是“大兴封建残余、挑衅破四旧运动、毒害贫下中农”。白梅当夜被捆绑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母亲被爷爷管得死死的,不许再哼半句昆曲,胆敢翘兰花指剁手指头。菊生死了心,嫁往几十里外做了上门女婿。03 我们生产队从没出过大富人家,更甭提达官显贵,至今做了最大官的惟数紧挨我家屋东的夏叔公。七十年代,他曾做过大队书记、乡里书记,九十年代初直升至县某局局长。我母亲说她小时候,读书很上心,成绩一直很好,而同队的其他女孩子悟性没我母亲好,她们的母亲眼红,遂纷纷在我爷爷那挑唆,说我母亲长得太标致,快要被别村的男人拐跑了。我爷爷听信了谗言,不许我母亲再去大队读书,但我母亲不依不挠着,多亏时任大队书记的夏叔公上门来劝我爷爷,说我母亲是块读书的料,应该用知识改变穷苦人的命运,最后父女俩作了妥协,母亲晚上去上夜校,白天照常出工挣工分。即便如此,我母亲读到三年级还是因农事太重辍学了,至今每每想起仍深懊不已,才更加劝诫我用功读书。我爷爷重男轻女思想很重,勒紧裤带供大叔读书,但他顽劣异常,上学时经常半路掏鸟窝,躲桥洞,荒废了学业,爷爷也只好作罢,把读书希望寄托在小叔身上,小叔读了小学上初中,半途辍学跟随我父亲学裁缝。我母亲最敬佩的人是夏叔公,倒不是他曾经强力为母亲争取求学的机会,而是文革时期,时任大队书记的夏叔公经常被揪出去批斗、戴高帽子、贴大字报,那年月被整得异常苦,但他依然开朗、乐观,干活、吃饭、睡觉如常,跟我母亲说的最多的话是:做人身正不怕影子斜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文革结束后,他恢复了工作和党籍,很快擢升乡里书记,仕途坦荡,退休前直升任县某局局长。母亲经常拿夏叔公的经历勉励我:做人,无论遇啥难关,一定要想得开,看得远。小时候,我爱转悠,流连于生产队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、旮旯里。有一次,下雨天,我看到夏叔公家门前井板下的水沟里,一丛丛的花开得茂盛,深沉。那花呈蓝紫色,花形似翩翩起舞的蝴蝶,袅娜在一片片肥厚、修长的叶片上,恰似一只只蓝色蝴蝶飞舞于绿叶之间,那花瓣一半向上翘起,一半向下翻卷,花心深处还长有三枚由雌芯变成的长舌形瓣儿。我从来没见这样娇艳的花朵,向夏叔公打听,他也不知花名。三十几年里,我一直把它当“无名花”。最近我在网上无意看到此花才知那竟是法国的国花——“鸢尾花”,寓意自由和光明,有“蓝色妖姬”美誉。我感叹了许久,心想,当年夏叔公身陷文革浩劫时,特意种下此花,许是为了每天提醒自己战斗不息、执着去追求自由与光明吧。我曾在席慕容的诗句中读到鸢尾花:“请保持静默,永远不要再回答我,终究必须离去这柔媚清朗,有着微微湿润的风的春日,这周遭光亮细致并且不厌其烦地,呈现着所有生命过程的世界……一如深紫色的鸢尾花之于这个春季,终究仍要互相背弃。”夏叔公退休后,常年居在县城里,家里的老宅一直荒废着,前年深秋,因孙女要结婚摆婚宴,他重新整饬了庭院,老宅重焕生机。去年起他常和老伴精心伺候着屋东一汪农田,过了把农作瘾。04 以前夏家湾的河水很清洌,甘甜。鱼虾很多,穿来梭往在水草间。河岸边栽满杨柳、楝树、水杉、乌桕树、槐树、梧桐树。夏夜,月上柳梢时,那明晃晃的月影穿过稀疏的树丛,投射在湖面上,斑驳一片。浜边,有好几个河埠头,每个河埠头上的石头被经年踩踏,早已光溜。盛夏时,河埠头异常热闹,黄昏时,大人们劳作了一天,趁暑气稍歇,纷纷在河边洗濯腿上的泥巴,小孩子则在水面上欢快地拍打着。小时候,一放暑假,我常常和生产队的小伙伴抱着木门栓、包装收录机、电视机的塑料泡膜,成天到晚,在河浜里扑腾着,渐渐地都学会了游泳。在河边蓊郁树荫里,我们学旱鸭子钻入水底捡河蚌,然后朝岸上的人用力扔去,引得岸上的姐姐、妹妹们争抢着,谁还一不小心捞起了哪家多年前沉入水底的菜刀、剪刀、火钳、铝锅盖、镰刀、斧子、镪刀。晌午后,烈日炙烫,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游出夏家浜,游到浜外偷对岸相邻生产队的瓜。我们猫在瓜地里,身手敏捷地翻着瓜叶,寻觅成熟的草瓜、黄金瓜、雪团瓜。谁觅到了,就邀其他仨坐在田埂上分着吃。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瓜农朝这边走来了,大伙纷纷扔下瓜,拔腿就逃,扑通几声跳入河里,一口气潜回了河对岸。瓜农站在瓜地里大声骂开了,我们听得捧腹大笑。肚子吃饱后,我们沿着泥滩,捉起了河虾,河虾稳稳勾在空心草上。我们两手轻轻一掬,河虾轻松被擒获。河岸边还常有专们为抓河蟹而支起的简易帐篷,夜深后,帐篷主人提着昏暗的煤油灯来蟹洞边寻视,用铁丝钩蟹,白天他们忙着去挣工分了。平静的夏家浜也曾吞噬过几个人,我家隔壁的婆婆洗衣时,不慎,滑入河里,无人看见。我大叔的儿子也在十岁时葬送在浜里面,记忆中的堂弟永远消逝了,留给叔、婶一生的遗憾和痛惜,伤痛永远无法弥合。冬天,湾边的树覆上了雪,玉树琼枝,晶莹剔透,宛如仙境,错落有致的冰凌,倒影在冰面上。这时沈姓一户人家要出发,摇乌篷船,敲锣打鼓着,迎娶新娘子去了。只见船楣上被披上浓重的红绸,船夫用船蒿在冰面上狠狠砸出窟窿,花了好久,才驶出封冻的浜湾,浜湾外,因水流湍急,没有冰封。新娘家太远,乌篷船又靠人力摇橹,到晌午,新娘仍未娶至,夫家人焦灼万分,不时在浜口朝远处张望着,那时又没通讯工具,不晓得那边情况。屋内等着喝喜酒的人也按捺不住了,来回往浜口徘徊、走动着。许久许久,不知谁兴奋地喊着看到船啦,看到船啦,夫家人拿出炮仗,在浜口热热闹闹地放开了,硫磺味在浜口瞬间弥漫开来,这时悠扬的磬锣声从雾气弥漫的河面隐隐传过来了,越来越近。乌篷船载着新娘子长途跋涉,终于驶入了夏家湾,泊靠在河埠头,红漆刷得锃亮的衣柜、洗脸架、椅子、桌子先被人喜上眉梢地抬上了岸,继而,好几个漂亮的伴娘簇拥着新娘子,走了上来,伴娘们手里都端着脸盆,脸盆里放着牙杯、梳妆盒、牙刷、毛巾,还有碗碟、枣子、花生。新娘羞赧着脸,低头细迈着小步,肩膀微微颤动,似是轻声抽噎。她手紧攥在媒婆的臂弯里。让出道的社民们越是凑近看,新娘头越低下,越发看不真切。我这时听见媒婆附在新娘子耳朵边,轻声说翠娥到夫家了,不必再哭了。刚说完,着藏青色呢料中山装的新郎福观迎上去,从媒婆手中,接过新娘子的手,在红火的炮竹声声里,迈进了自个家门。拜天地时,七娘娘和几个婶嫂轻声议论着新娘的婚衣,从面料一直说到款式。新娘子上穿织锦软缎襟盘扣棉袄,这是我父亲缝制的,前几天晚上,他为了赶工,在家里缝制得很晚,单那对襟盘扣就反复做了许久。父亲会做很多的盘花,这是古老中国结的一种,又叫盘纽,连接衣襟,用布条盘织成各种花样,他总会奇思妙想地选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吉祥意义的图案,且不断琢磨着新花样,有模仿动植物的菊花盘扣,梅花扣,金鱼扣,还有寿字扣,双喜扣。我也看到好多次生产队里嫁女的盛况,新娘子出发前,总在父母、哥嫂、姊妹面前哭得梨花带雨才作罢,她的母亲和嫂、妹们也陪着哭,据说哭得越悲哀,越发表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及对亲眷的爱,将来婚姻越美满幸福。八十年代中叶,挂桨船慢慢替代了人力乌篷船,速度更快,不用这么大清早出门迎亲了,根据亲家远近,从容地安排迎亲出发时间。在很长时间里,我们生产队都是从这湾里迎娶新娘来,也是从这湾里将姑娘们嫁出去。九十年代初,生产队后面通上了东西大道,交通更便利了,挂桨船也退出了迎亲队伍,湾边小路也不再是交通要道,但哪家迎亲嫁女,也都要从湾边走一遍,似要让夏家湾的列祖列宗们都一一看到,蒙受庇佑。05 我在夏家湾渡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。上初中后,我住宿在校,回乡下少了。一九九五年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,日子过得特别漫长,我焦灼地等候结果。得知高考成绩是某一天的下午,我急奔着往家赶,想尽快将高考结果告诉父母。母亲这时正在湾边的河埠头上洗衣服,我朝母亲欢叫着,嘴里嚷嚷着我考上了,我考上了,母亲仰起头,绺了绺头发,朝我欣慰地微笑着,这时湖面的波纹漾开了,漾得很远很远,黄昏中的余晖,穿过影影绰绰的树丛,揉碎在潋滟波光里。工作后,我和妻儿吃住都在县城,一年里已难得睡在乡下。前些年,镇里开始建设“美丽乡村”,疏浚河道,整治村貌,浜里、浜外的水葫芦、杂草等杂物被清撩一空,浜岸也重新整饬,水面变宽畅好多,夏家湾里的河水变清了,恢复到了儿时的模样,水波清漾,消失的鱼群也回来了,河边铺上了鹅卵石径,新栽上了观赏树种。夏家湾似一枚深深嵌在我心底的图钉,无论我走到哪里,内心都装着它。将来,终有一天,我也会从远方,回到这里,久居于此,就像夏雷荣叔公一样,如今已叶落归根。我在宣纸上眷下一行字:愿得一方水,一生为知己;愿守一道湾,白首不相离。-本文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- 行走海盐散文随笔原创诗歌 海盐民俗原创小说色彩活动 END 很多记忆是模糊的,唯有文字是清晰的。如果今天没有遇到最好的表达,那也没有关系——至少,这样的时间,我们有过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投稿邮箱:yueduhaiyan.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ihuadidinga.com/zhddrybw/1051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如何通过科学服用中药,提高自身免疫力,预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