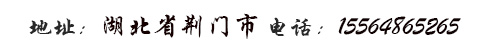天下美文刘梅花古凉州马事
|
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郑华国 http://disease.39.net/bjzkbdfyy/210922/9475681.html 古凉州马事 文 刘梅花 凉州大马。 古凉州最好的马,叫天马,是走马,走对侧步,不走交叉步。高臀,硕蹄,细腿尖耳,粗鼻孔。鼻孔大,吞吐量大,体健善跑,耐力好。凉州出土的天马,昂首嘶鸣,看一眼,乖乖,好大的气势。这种漂亮的好马,历史上叫凉州大马,现在河西走廊有,青海有。 实际上,古时候很长一段岁月,整个河西,青海的部分地区,都是属于凉州的,所以叫大凉州。青海和凉州,常来常往。青海花儿《下马关令》里这么唱:好马上备的是好鞍子,鞍子上骑的是人梢子。祁连山来胭脂山,牧民占下的好草山。甘州不干者水滩滩,凉州不凉者米粮川。肃州的坳子嘉峪关,西宁的坳子是燕麦川。可见当时青海和凉州不分彼此。人们从青海到凉州,骑马就来了,串门一样。老话说,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。这大马,包括青海的菊花骢大马。 现在呢,河西的山丹军马场有毛色纯白如玉的好马,天祝藏区岔口驿也有优雅的紫骝走马,青海有漂亮的大青马。这几个地方的宝马,来源都是西域的大宛马,虽然叫法不一,但追溯上去,汉朝都叫天马。 我们岔口驿的走马,高大威猛自是不必说了。古时候它们是战马,眼神冽,细腿子有劲儿,气势浩大。走马临阵无敌,一声嘶鸣,如猛虎下山,霸气啊。多是紫红色,腕蹄高,宽大,一蹄子能刨掉战车。铁尾,一尾巴能扫翻人。马蹄大而硕圆。蹄腕里一撮老毛,走路又快又稳。它的鬃毛极长极硬,若是不辫吉祥扣,能拖在地上。那时候阔人家的马夫,最耗时的活儿就是在河里给走马洗刷了鬃毛,慢慢辫成吉祥扣,打理清爽。至于戎马和驿马,直接剪短鬃毛就行了,没工夫啰哩巴嗦地侍候。走马的胸廓很发达,吃着鲜美的牧草不说,还要吃料。料就是豌豆。岔口驿古来就是驿站,驿马也多。走马性子野,喜欢在山野里撒欢乱窜,腿筋拔得开,蹄腕灵活有力,走起来轻捷平稳,是很好的驿马。 山丹军马场的天马,有走马,也有跑马。风驰电擎,像紫色的白色的青黑色的闪电一闪而过。古时候金贵得要命。此种马是从西域大宛国来的,白的一身纯白,毛色清冽。紫红的透着贵族的气质,青黑的毛色厚实,针毛闪着亮光。它们的耳朵很小,竖起来,眼睛却出奇地大,腿子细长,马蹄尖细玲珑。这种马是西域野马的后代,性子烈,立鬃长尾,只认主人,陌生人不能近前,很警惕。上战场即便败了,对手也很难调服使役,一有机会就挣脱笼头,跑回自家地盘了。它们喜欢吃苜蓿草,在夜里也能识途,翻山越岭也不迷路。 青海的天马叫菊花骢。骢,意思是青白色的马。高大,健壮,俊美。毛色青白,脊背和前胸有着圈纹,一朵一朵,针毛张开,像极了盛开的菊花,层层叠叠,好看得要命。此马通人性,能护主人。十里外能闻见陌生人的气味,一蹄子能踢死一匹肥狼,连狈也能踢飞。菊花骢通体都是一种霸气威严的大气场,眼神萧杀冷峻,走对侧步。所以,青海人出门骑上一匹菊花骢,就跟你上路开着宝马一样,都是风光无限。不,还是不一样,再好的车,都是呆滞的机器。而好马,那是鲜活有灵魂的,这个没法比。主人受伤了,菊花骢用嘴能把人拉扯到马背上平安驮回家。就算驮不到背上,会飞驰回家,悲苍焦急地嘶鸣着报信儿。这个,宝马车们是打死也做不到的。 人生最得意的事情,莫过于打马飞驰,一路踏花。春风得意马蹄疾啊!今天所有的徒步跋涉,就是为了在未来的光阴里遇见骑马的自己。最好,骑的是菊花骢,连大白马都不要。 青海有一首很好听的《尕马令》,是这么唱的:墙上开花者碟子大,地下的骨朵儿碗大。维下个花儿者兴头大,半上午没喝个早茶。哎吆吆……阿哥是阳山的枣骝马,尕妹是阴山的骒马,白日里草滩上一处儿耍,晚夕里一槽儿卧下。哎吆吆…… 最早的菊花骢,据说是吐谷浑人的坐骑。《隋书》说:吐谷浑有青海,中有小山。其俗至动辄方牝马与其上,言其龙种。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,因生骢驹,日行千里,故世称青海驹。 据说,唐朝有一种舞马,就是从青海进贡的。马体柔和,闻乐起舞,舞姿蹁跹,眼神妩媚。马能舞蹈,本身就很妖孽了。到后来,被看作是亡国之兆,灭绝了。 也有记载说最早是羌人驯化降服了野马。驯服的马,都被戴了笼头。还有嚼子,我们河西叫岔子。一根皮条或者是铁链子,卡在马的牙齿里,大概位置在切齿与臼齿之间的空隙。这是马的软肋,牵动缰绳,嚼子刺痛马嘴,很疼,疼得它掉眼泪,只好驯服了。 我总是觉得,不是人类降服了马,人没那么强大。而恰恰是马的悲悯之心,多情之心。古人说,不俗即仙骨,多情乃佛心。比起马来,人长得弱小,欲望又那么庞大。马所求的,无非是水草丰美,自由自在,它连肉都不吃。而人呢,饿了要吃粮食,吃了粮食要吃肉食。天上飞的,地下跑的,张大嘴巴狂吃。还要有高楼大厦,还要有金银绸缎……无情无尽的欲望,没有界限的贪婪,靠着人单薄的身体来完成,又苦又累。马看着人可怜,这些驾驭不住自己心的生物,决定帮人一把。 我见过一匹发怒的青马。它驾着辕,拉着一辆木头车子,正上坡,速度也不慢,却挨了几鞭子。那人歹毒,鞭子是牛皮条里裹挟了细铁丝,抽在马背,一鞭子一条血路。这匹大青马被激怒了,它暴躁起来,腾空而起,几蹄子踢碎了架子车,挣脱了身上的枷锁,嘶鸣着,带着鞭痕绝尘而去。那一刻,惊心动魄,架子车像纸片纷飞,那个折磨马的人,早叽里咕噜滚到路边坡下去了。 马也会哭。懒人家,冬天没有好黄草,草铡得也粗糙,咽不下去。又没有豌豆加料,特别累,天天干活。到了春乏关,接着拉车耕田,连一口麸皮也不得。它疲惫地拉着车,一边走一边淌眼泪。背上挨了一鞭子,清眼泪水一般地流。人们最大的感恩,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。可见,做马本身就蕴含着回报之情。我爹说,所有的牛马都是来报恩的,善心肠。 有时候,一匹马也是很孤独的,它眼神清澈宁静看着你,把脑袋靠近你。在它看来,你不是主人,是朋友,给它温暖的朋友。更多的是,人并不了解马的思想,除了奴役,再无柔和。于是,马一直孤独着。 马鞍子。 好马配个好鞍子,俊女子嫁个人梢子。这话经常挂在谁的嘴上?不是骑手,也不是开鞍鞯铺子的,是媒婆。媒婆有点老了,走不动路,就骑个毛驴。没有鞍子,就在毛驴背上搭一条牛毛褐子,骑在毛褐子上一颠一簸赶路。 你想,鞍子很贵啊,毛驴,骡子,黄牛,就都算了吧,留给马好了。那时候,我家想养一匹马,爹感叹一声说,马能买起,鞍子置不起呢。于是,买了一匹栗色骡子,一样拉车犁地打场,还不用鞍子,就是脾气倔点儿,动不动尥蹶子。 让一匹骏马来干农活,多少大材小用了,马会感到憋屈的。尤其是打场,那么漂亮的红鬃烈马,套了石头磙子,一圈一圈转磨磨,多郁闷呢,简直怀才不遇啊。烈马嘛,要驰骋,要在大草原上鬃毛烈烈飞驰而过,骑手都是俊朗挺拔的人梢子,那才叫痛快洒脱。窝在田地里拉犁铧,绕在打麦场上拉磙子,算什么事儿呀。 古时候不好的马,叫驽马。这样的马,就是跑不快的马,有点懒的马,累垮了的马,生病的马,都叫驽马。它们身份不高贵,用来驮茶叶垛子走茶马古道,也用来拉车耕田被奴役着。但在我们河西,没有驽马的说法,马只分两种,跑马,走马。在我们藏区,没有人会吃马肉的,只吃自己供养的牦牛猪羊。马死了,就掩埋了,让它平静归于大地。 去岔口驿串门,眼热人家的好马,气宇昂扬的,想摸一摸。可是主人却说,你看,这套鞍鞯才是最最好的呀。鞍是鞍子,也叫鞍桥,长得像桥。鞯是托鞍的垫子。一套华贵的鞍鞯,是半匹马的价钱。鞍辔,鞯汗,鞯勒,鞍韂,都是好匠人好材料精工雕琢的。还有马嚼子也是马鞍必须配置的。 最初的马嚼子,是坚韧的皮革。后来,变成是铜铁的链子,和缰绳有牵连,牵扯进马嘴巴里。驾驭马,骑手根据自己的心思来控制马行进的速度。因为马有野心,不喜欢被人驱使,有了马嚼子,它会驯服一些。成语有分道扬镳,镳,就是马嚼子,两条缰绳和镳相连,各走各的道。 好马鞍,不用铁骨架,就是用整块的桦树根雕琢打磨而成。用铁骨架,一来重,二来磨伤马背,让马焦躁不安。根雕的木头马鞍,打磨得光滑柔和,有韧性。前鞍头高,后鞍头低,鞍头大,鞍桥宽,轻而舒适。鞯是挼好的硝牛皮,柔软透气。鞍座是七彩的羊毛氆氇毯。黄铜马镫,细嚼子。羊毛毡上镶了氆氇包边的汗鞯,牛皮的肚带,羊皮制成的马鞦。笼头是软皮条挽的,连缰绳也是羊毛编织的,甭提多么豪华排场了。有的人家,还有马褐,牛毛编织的护衣,天冷了给马御寒。 你想,紫骝马上配上这样好的马鞍子,如果骑马的小伙子俊朗挺拔,不是人梢子是谁呢?姑娘们看一眼都心里喜欢得放不下了。吾乡人卖马,价钱都不说出来,袖里吞金,在袖子里捏指头。袖子窄了,不好捏,就撩起衣襟,躲在衣襟底下捏指头讨价还价。口袋里卖猫,隐秘而奇特,一句话也不能说出来,不动声色看着对方的眼睛。 旧时,河西一路都是车马店,门口有拴马桩,马槽。我刚到镇子上时,还有一家车马店,门口的杆子上挑着一束黄草,招牌上写着:道道店。正门很小,后院却有一个很大的门,供车马进出。去年回去看,拆掉了,改了榨油坊。 没有鞍子的人家,出门就在马背上搭一条毛毡,或者褥子,骑马出门。据考证,最早的匈奴人也没有鞍子,用软牛皮裹在马背上当鞍子,或者搭一张羊皮。 凉州出土的马鞍子,是汉朝末年的。彩绘木雕马鞍。在雷台,和铜铸天马一起出土的青铜天马们,马背上没有马鞍子。没有鞍子,不是说明那个朝代不具备马鞍子,应该是有的。只不过,天马是烈马,神马,铸造的时候不备鞍子,是象征一种腾飞的自由和野性,不被束缚的豪气。一旦有了笼头和鞍子,就是一种驯服和低头,而不是天马行空的豪迈气势。现实和艺术,总是有点距离的。 马镫。 其实,马镫这家伙是挺重要的,不信啊? 马镫踩脚的叫镫环,古时候是木头雕刻的,后来换了铜铁的。也有木头骨架,黄铜包边的。悬挂在马肚子两侧的,叫镫穿。整个马镫,牢牢系在马鞍上,不可疏忽大意。系的带子是柔韧的牛皮条。游牧民族更加重视马镫,最早是用绳索皮条编织的套环,当做马镫。 没有马镫骑马,那可就不飒飒英姿啦。马很野性,慢走一段路之后,就一溜烟小跑,然后狂奔。若不是马嚼子束缚一下,它连飞的心都有。你想啊,连个马镫都没有,马跑那么快,你的双脚悬空吊着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随时有可能滚下去。只好双腿夹紧马肚子,抓紧马鞍子才能狼狈逃窜。这样的状态,若是两军对垒,打起仗来,前程恐怕很不美妙啊。 若是单单骑马去溜达,串门走亲戚,不需要马鞍和马镫也可,搭一条褥子,双腿勾住马肚子,就可以保持马背上身体的平衡。若是马太肥的话,而骑马的人腿子又短,就费力些,但不影响行走,好赖能驮着走村串巷。但是,在古代,马最重要的功用不是拿来消遣串门的,是打仗。厮打的时候没有马鞍和马镫,直接打不起来,马跑得快了士兵就会掉下来。不用人打,对方放出来一群狼直接狂撵,可以撵死一大群人马。 马鞍和马镫,是骑兵绝对的依靠。最好的马鞍是高桥马鞍,马鞍牢牢地固定骑手在马背上的位置,他可以随意转动身体而不掉下来。马镫让双脚牢牢的支撑,还能辅助驾驭,纵向横向的活动范围都伸缩自如。 汉朝得到大量宝马之后,兵士们只要在马上训练一段时间,就可以骑马作战,毫无生涩感觉。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人马,相当的厉害,威武凶猛,就是骑兵很强大。 汉朝为什么老要和匈奴打仗呢?因为匈奴人剽悍,很轻易地降服了野马,野牛,降服了很多的小部落。但是他们降服不住自己的心,总是想着汉朝的东西好啊,食物好啊,就忍不住犯边抢点儿东西。他们的马匹好,有鞍子,还应该有马镫。为什么呢?匈奴骑兵,善用一种兵器叫“经路”,是一种刀,主要靠速度取胜,很凶悍。致命的打击是靠砍,劈的进攻。这样一来,除了马鞍能稳定身体平衡之外,必须有马镫。没有马镫,无法完成这一整套动作。 秦始皇也打过匈奴,大将军蒙恬率领四十万大军,又筑城,又修长城,又移民,才把匈奴拒绝在长城以北。蒙恬的将士善用长戈。远距离持弩放箭,近距离长戈点刺,有战术。也有马车助阵,抵御对方的骑兵。秦朝的骑兵都是骑马冲击敌人,让匈奴阵脚大乱。马上追击敌人,追到跟前,跳下马作战。秦人的长槊实在厉害。下马先用长戈刺伤马腿。这样,匈奴人的兵器短,缺陷就来了,招架不住长戈。秦人高大强悍,有完美的布阵和战术,又因为体健善跑,箭射得非常好,所以匈奴才被撵走,也是不容易的。 匈奴和秦人交战时,马镫应该是绳索,牛皮绳,牛皮套这类东西做成的,软,晃荡,不稳定。长槊直接可刺伤马背上士兵的脚,打击很致命。马镫不能保护脚,所以匈奴也被迫是跳下马来厮打的。可是匈奴和汉朝交战时,作战能力强大了很多。来无踪,去无影,甚至可以骑在马上回头拉弓射击追击的汉士兵。没有马镫,或者马镫不够稳当,回头射击这个动作是完不成的。 飞将军李广,骑术箭术,独步天下。他在马背上装死,追兵近了,突然翻身朝后一箭,紧接着又一箭,箭箭无虚射。没有马镫,他无法达到骑在马背跟平地上一样,轻松自在。总以为,这样的人,是有奇异的东西在协助,不仅仅是马鞍马镫的功用了。也许,他是苍天打发来做大事情的,一般人,打打酱油而已。 马鞍固定了纵向的稳定,在飞驰时可以向前方射箭。如果掉转身射击追兵,横向没有稳定的支撑,还是会掉下马的。那么,马镫是肯定有的,而且不是绳索皮条的,它牢牢固定了横向的稳定,从容射箭。由此可推断,匈奴的马镫做了改进,从软的马镫,改进到坚硬的木质或者铜铁的马镫了。 汉武帝坚毅勇猛,被匈奴骚扰的快要气死了。他憋了一口气,最初先派遣人从西域买马,不得。但是,得到了西域的好草,苜蓿。宝马必须要好草,一般的草它们不吃。匈奴的马匹在草原上,吃的是质地优良的牧草。中原大地,只长庄稼,没有好草场。但是苜蓿是可以种植的,宿根,今年种了,明天接着割,不用担心。一茬割了,又一茬长起来。苜蓿草有紫花和黄花,紫花苜蓿最好,做菜吃也好,我小时候经常吃。嫩芽剪来,开水烫了,凉拌,口感好。都说马无夜草不肥,其实光有夜草不行,还得吃料。料就是粮食,豆类最好。但是,吃苜蓿草是完全不必要吃料的,马膘肥体壮,力气大耐力好。 中原的苜蓿草长得有了规模的时候,汉武帝也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好马。他激动地吟了一曲《天马徕》,表达自己内心的狂喜。宝马有了,一切都会有的。汉朝有的是能工巧匠,马鞍马镫自然会打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于是,汉朝大名鼎鼎的将军,封为骠骑将军,此人便是霍去病。骠骑两个字是很有深意的。 骠骑将军对马嚼子也做了改进。马嚼子由两根铁杵的扣接,变成细链子,而且两侧加了耐磨而韧性好的皮条,贴在马腮,这样不会因为长时间的驾驭而磨伤马嘴头。 因为马匹的繁衍,汉朝从秦人的组合车骑发展成单独骑兵,更加灵活,作为军队主体。卫青和霍去病都是老天派来的奇才,他们使用庞大的骑兵集团,除了打磨好马鞍,还给马鞍添加了鞯,就是托鞍的垫子。因为这张垫子,使得马背很舒适,不会磨损马背,不会使马匹疲劳。天马的耐力是无可比拟的,好的马鞍,马镫,马嚼,使得汉朝的骑兵声名显赫。 有了马鞍马镫,骑兵仅仅用缰绳控制马匹就行了。训练良好的军马,直接听口令就可驰骋作战。骑兵的阵很重要,八卦阵啦,撒星阵啦,雁阵啦,钩阵啦……可以集中冲击,打击力度很大。汉骑兵的防守也很厉害的。匈奴骑兵扑来,他们突然间散开,如星在夜空,密而不聚,使敌人扑空。等匈奴泄了攻气后撤时,散开的士兵倏然间聚拢过来,猛力扑击敌人,长矛直接砍马腿,屡战屡胜。这样的战术,凉州大马的功劳实在大。 除了马镫马鞍,骑兵还有盔甲来保护自己,增强射箭能力。若是没有马镫,骑兵若是一只手牵引缰绳,一只手操作刀箭,重心不好控制,那打仗就很难的。而且若是对方使用长矛马槊,失败的几率太高。 汉朝的主力兵种由步兵转换为骑兵之后,开始大规模的出兵河西,收复失地。于是,霍去病和卫青开始发起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。 据历史记载:元狩二年,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。率兵出击河西的匈奴浑邪王、休屠王部,大胜。从此,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,打通了西域道路。匈奴忧伤地唱着歌谣迁徙而去:“失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自此,“匈奴远遁,而漠南无王庭。” 当然,河西也不是匈奴的老巢,他们也是从别的部落里抢来的。汉朝的反击不是突然之间的心血来潮,而是有着漫长的压抑和愤怒。 细读他们征战,很显然,马鞍和马镫是细节决定了大局。因为有良好的配置,骠骑将军的骑兵体力充沛,夜袭匈奴右贤王的时候,骑兵悄无声息边接近了敌营,因为马鞍很舒适,马匹不会被磨损,所以长途奔跑不疲劳。因为马镫和马嚼配合默契,马匹听从指挥不乱阵脚。厮杀的时候,两头高的木制托架马鞍,保护了兵士的作战。 而且霍去病很懂马道。他选择春天进攻。我们牧区说,牛马春天要过个春乏关。一场大雪,马匹无草,不饿死就不错了。你想匈奴人主食肉,春天的牛羊乏困,枯瘦无肉。这个时候,人困马乏,草青的消息还很遥远,大汉将军霍去病却乘风而来。他简装轻骑,吃足苜蓿草和豌豆的宝马一路疾驰,后续供养粮草充足,无后顾之忧。 就这样,霍去病长驱直入,切断匈奴右臂,列四郡据两关,西接西域,汉王朝有了河西之地。河西古道,长路漫漫,成为后来的丝绸之路。西域诸国的使臣,栗特人的商队,西域的僧人,就从这条古道,走进东方古国。河西沿途,驿站,窝铺车马店,商市,酒肆,逐渐热闹起来。 马镫出土的实物没有很早的。大概,最初的马镫是皮条木头的,所以很难保留下来。有些壁画上倒是有,很模糊的一个轮廓。 河西是古代的边关之地,随处可见千年的古长城。有征战,就有生态的破坏。河流改道,树木砍伐,良田会变成荒漠戈壁。但是,古凉州的大马,是汉唐时候的坚守,若无凉州大马,汉唐不知道要多辛苦。人生的财富有大有小,人生的资质有高有低。穷,不足悲,因为土地贫瘠,河西人朴实,虽贫,却心平气和。你知道,河西的志气和骨气,都在凉州大马的脊背上载负千载又千载。 (本文选自年《山东文学》8月上半月刊) 《山东文学》投稿方式 年《山东文学》订阅方式 1.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,邮发代号:24-3 也可扫码或者长按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ihuadidinga.com/zhddrybw/1115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天丁与健康
- 下一篇文章: 学讲话谋振兴闯新路做好三篇大文章乳